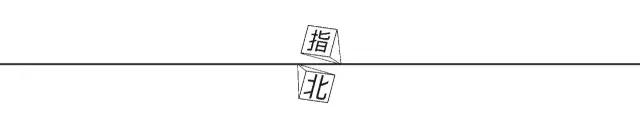“穷,但优雅” 互联网人吐槽“亲戚”的套路和心态
如果说网络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流行一种政治正确的舆论导向,那么过年期间最正确的姿势就是“吐槽亲戚”。
从年前春运开始,一直到大年十五闹元宵,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“亲戚”的吐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玩命量产:有亲戚们不可理喻的三观,有老家令人费解的风俗,还有自己迫不及待离开家乡的糟心故事,仿佛所有人都在参加“怒其不幸,哀其不争”的经验分享报告会。
这样的舆论氛围让人感到焦虑,对于笃定要回家过年的人来说更甚,比如我。
习惯了每年回家的我忽然发现,自己的老家就是段子里描述的“十八线小城市”,亲戚们确实拥有“无法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”的中华土味三观,再加上一线城市漂、贷款买房、尚未婚配、没进体制等一系列标签,“我”似乎已经成为了行走在亲戚之间的活靶子,即将把段子变成生活。
然而假期过去了,公司也开工了,亲戚们都各回各家了,当初在网上学习的各种套路不仅一个没用上,甚至让我有了另外的感想:
“别都看不上老家的亲戚们,你们只是穷但优雅而已”
60岁的老舅劝你进体制?
有人把过年时亲戚们烦人的“关心”大概分成了两种类型:一种是证明你过得不如我好,满足自己来之不易的优越感;另一种是知道你过得很不好,释放自己快要泛滥的同情心。
前者之所以让人讨厌,是因为这样的亲戚会试图用自己的三观来判断你的三观,属于观念冲突;后者之所以让人讨厌,是因为这样的亲戚并不会有建设性的建议,属于浪费时间的无效关心。
不让自己那么糟心的办法也有,比如少跟亲戚们见面,就可以有效避免两种情况的发生。然而过年的一项重要流程让与亲戚们的正面对垒变得在劫难逃,那就是年夜饭。
年夜饭的饭桌承载了绝大部分的撕逼剧情,虽然我家的年夜饭规模不是特别大,但人员附带着的标签构成已经足以支撑起任何一部国产家庭伦理剧。
先来说说我的老舅。我的老舅是标准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工人,50年代出生,完整地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,从此对红薯一类粗粮深恶痛绝。下乡插过队,组织推荐当过工农兵学员,参加工作后在国企当了一辈子产业工人,人生轨迹单纯地像春晚的小品,几个红头文件组成了大半辈子的生活。
按照段子里的剧情,酒过三巡之后的老舅应该在饭桌上这么教训我:
“网上的那些工作都是骗人的,前几天我还在新闻里看到好几个什么创业的,骗融资最后都跑路了,你这公司名字我都没听过,到底靠不靠谱啊?你还是考虑考虑回厂里吧,厂办还缺几个秘书,干几年出来之后都是当官的……”
而我应该这样大快人心地怼回去:
“其实我也挺想回厂里的,可最近看报纸吧,老工业基地都在经济衰退,以前那些看着还不错的企业不是破产就是裁员,也挺危险,咱家没有波及吧?听说最近已经连续好几年报亏,过年连个红包都发不出来了……”
但实际上这个我精心准备好的套路到散席也没用着,原因就在于老舅今年换成了舅妈用剩下的 iPhone6 ,开启了全新的4G手机时代。于是,在除夕夜当天的年夜饭上,他不仅熟练地刷过年红包、以最快的速度集满了五福,还学会了入口被深埋(相对于抢红包)的AR红包,带着七大姑八大姨们满屋子转,低头族们瞬间开起了运动模式,对我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并没有什么兴趣。
乍一看这样奇特而又热闹的使用场景,我们是不是错怪了产品经理们?
离异打拼的姑姑说读书无用?
在很多人看来,有些“理所当然”的事情是不需要过多去证明的:比如老家的亲戚们肯定是互联网菜鸟,比如亲戚们的朋友圈肯定满是谣言,比如亲戚们的手机里只有微信QQ和快手,比如我姑姑这样的人肯定是个“读书无用论”、“文人穷酸腐”的支持者。
我姑姑出生的那个县城,90年代之前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只有水路和坑坑洼洼的盘山公路,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才有高速通车,可以说非常闭塞。老公是个标准的赌徒,整天游手好闲还时不时家庭暴力,结婚时还比较殷实的家底很快就被败光,姑姑一忍再忍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婚,自己下海经商,一门心思地挣钱。如今事业有所小成,回老家过年都有衣锦还乡的意味。
按照段子里的剧情,酒过三巡之后的姑姑应该在饭桌上这么教训我:
“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啊?我现在挺心疼你们这帮90后的,好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去我那儿,拿到手里的现钱四千不到,根本存不上钱。你要是早点出来跟我做生意就好了,时间都浪费在读书上头了,网络一断你们都找不到饭吃。”
而我应该这样大快人心地怼回去:
“是啊,我也觉得应该早点下海做生意,浪费那些学费干嘛。这四年大学真把我变成穷小子了,啥也不会啥也没用,也多亏女朋友不嫌弃,要是结婚了我肯定好好赚钱养家,绝对不像个别人似的,啥本事也没有,就会打老婆。”
但实际上这个我精心准备好的套路到散席也没用着,原因就在于姑姑的实体经济也面临着资本寒冬的考验,互联网工具的试用让生意有了回暖的迹象。于是在除夕夜当天的年夜饭上,姑姑分享了她通过社交平台的运营在维持核心用户的基础上,吸引到了过去覆盖不到的用户群,还邀请我给她的新店做一波“线下地推结合线上活动”。
乍一听:这不是社群媒体的玩法么?
易祺互联为您提供:商城系统,智慧物业管理系统,“好差评”系统,食品溯源系统,智慧点巡检系统,农村电商系统,智慧河道水位监控系统,智慧环境监测系统,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,ERP系统,智能建站系统,商城系统,直播系统,各种软件/网站定制开发,网站托管等一站式运营解决方案。
易祺互联 @ 河南蓝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运营品牌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101055710161107
软件设计部运营中心: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芯互联大厦南座11层
智慧物联网运营中心: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1号河南省人民会堂
新产品培育运营中心: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25号经津大厦10楼
北京市(华北区)运营中心: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33号清华大学学研大厦B座10层
广州市(华南区)运营中心: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汇四街11号
杭州市(华东区)运营中心: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杭州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中心A座10层
重庆市(西南区)运营中心: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联东U谷12栋
业务咨询:0371-60934100 手机:18737894979 国内热线:400-8778-670
技术服务:15516975329 投诉热线:185-38935-211